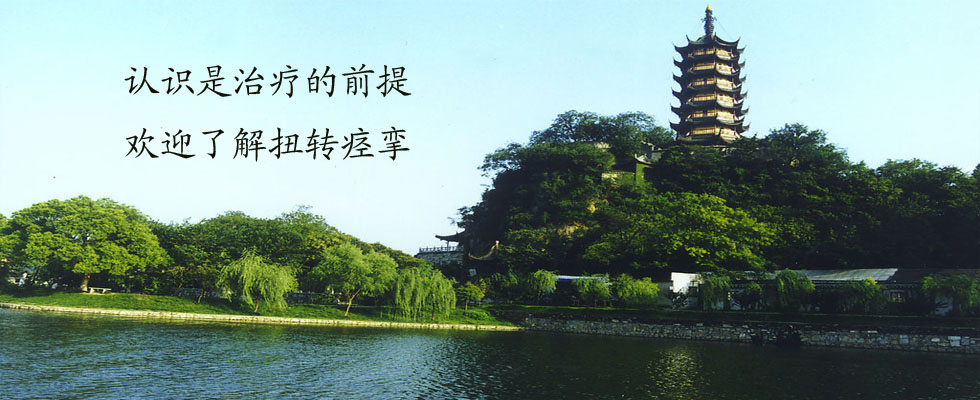来源:醉美玉兰
手术室内心跳骤停:麻醉医生复苏与管理----第一部分
高级生命支持(ACLS)是基本生命支持(BLS)的延续,最初ACLS是用于管理在社区突发心跳骤停患者,随后经改良或修改引入院内心跳骤停患者。最初,ACLS和BLS是为突发昏倒或被发现无反应的患者制定的。BLS是ACLS的基础,而ACLS在ECG和充分循环的临床征象下有序管理。ACLS专注于处理心跳骤停的常见心脏原因,包括心脏转复、除颤和药物来恢复自主循环。关于手术室内心跳骤停和危机管理,前期的文献给予了陈述,最近关于围术期心跳骤停和其他危机方面的文献综述更新了ACLS。而本综述包括2部分旨在从临床角度对围术期心跳骤停管理进行了更新。第一部分,对围术期心跳骤停的原因和结局进行了概括、对围术期患者复苏方面理念进行了综述、提出了围术期心跳骤停管理和预防的流程。第二部分,针对具体麻醉相关和围手术相关危象的管理进行了探讨。
在围术期一般是目击下的心跳骤停,且产生原因通常知晓,因而围术期心跳骤停与其他环境下的心跳骤停明显不同。与其他心跳骤停相比,反应更及时、更具有征对性(专注)和原因可逆性如药物副作用和气道危象。对手术患者进行治疗的医护人员(caregivers包括术者、麻醉医生及护士等)通常了解患者相关内科疾病史,并目睹患者病情危象自数分钟至数小时演化过程;积极采取措施对症支持治疗以避免或延缓ACLS需求。在决策共享的时代,对特殊病人需要一些强化治疗,而这些恰恰又受到患者和家属对这些积极处理措施期望理解所限。
共识产生方法
邀请国际上12个围术期复苏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目前的围术期心跳骤停和围术期危象方面的证据进行文献复习和评估。挑选专家的标准如下:(1)在麻醉与围术期管理方面的临床经验;(2)在围术期危机和复苏管理模拟培训方面有所涉猎;(3)熟悉国际复苏指南;(4)国际影响力(为确保本推荐在多个临床平台很容易转化为床旁实践)。专家组通过电子邮件、面对面和必要时的电话进行交流。挑选文献复习的文章囊括了自年以来的指南(指南中提及文章进行再次核对)和相关文章及PubMed上可查到的相关主题。委员会中意见分歧尽量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余下的分歧通过其中的两位作者(V.K.M和M.F.O)进行判别决定。
围术期心跳骤停的原因
对于循环危象和心跳骤停具体原因在围术期与院内、外条件下显著不同。外科操作的迷走反射、促迷走张力的麻醉药、麻醉药的交感抑制、?受体阻滞剂、椎管内麻醉导致的T1-T4心加速神经纤维抑制是围术期心动过缓的常见原因。由困难气道导致的低氧是手术室内心跳骤停公认原因。手术中大失血患者心跳骤停的常见原因是低血容量引起的无脉性电活动(PEA)。造成循环虚脱围术期特异性和更泛鉴别诊断原因还包括:麻醉药方面如吸入或静脉麻醉药过量、椎管内麻醉、局麻药中毒、恶性高热;呼吸原因如低氧、自主呼吸末正压和支气管痉挛;心血管原因如血管迷走和眼心反射、低血容量休克、气栓、腹内压增加、输血和过敏反应、张力性气胸、起搏器失败、长QT综合征和电惊厥治疗。
围术期心跳骤停的预后
在过去的5年里,多项研究报道:与一般人群或住院患者相比,围术期心跳骤停后患者存活率增加。另一项关于手术患者的促进生存统计,存活率最低(20%)患者群包括:老年、高ASA分级、急诊、污染伤口和术前高度依赖的病人。以前研究报道心跳骤停后存活低多发生于晚上和周末。尽管似是而非,相比手术室和ICU,发生于PACU的心跳骤停后存活率和神经功能较好。可能与发生于PACU心跳骤停不同原因相关。
最近发表来自国家麻醉临床结局登记心跳骤停数据分析显示麻醉相关心跳骤停发生率为约5.6/(/),较以前估计要低得多。这一数据也提示:随年龄和ASA分级增加,心跳骤停发生率增加;而出乎意料的是,男性心跳骤停和死亡率更高。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手术后24小时内心跳骤停最常见心跳骤停ECG类型为窦性停搏。而围术期窦性停搏存活率(30.5%-80%)显著高于住院患者(10%)。
心跳骤停前认识
对麻醉医生多项调查表明麻醉医生对基本的和麻醉相关的复苏和心跳骤停知识缺乏。一项研究显示在围术期对可电击心律失常,电转复和电除颤存在延迟。为使处于危机中的患者得到有效救治,围术期医护人员必须识别患者危机状况并开始有效处理。由于患者处于镇静或全麻状态(除非对患者精神状态进行充分的监测)、实施控制呼吸(防止呼吸过快或停止)、手术体位使评估更加困难(侧卧位、俯卧位、陡头低位)和身体大部分被手术敷料覆盖等,围术期识别患者危机状况更加困难。没能对患者的危机状况进行及时补救是经常导致心跳骤停和并发症/死亡的原因,也是常见的对当时所作处理评估的事后偏见的结果。当能进行补救时,肯定会发生心跳骤停的频率还是比预期的要少。在多数(最有可能)情况下,危机状态及其严重,以至于即使及时采用了最大程度支持治疗,患者的死亡也不可避免。
强化治疗
强化治疗包括采用更高级别的监测和高级支持治疗措施。采用更高级别的监测或评估取决于患者病史、目前临床状态、麻醉和手术情况。进行有创监测时不应延误支持治疗,几乎所有的不稳定患者都应进行有创动脉监测。当需要中心静脉压监测或静脉氧饱和度监测指导复苏,或医护人员预测需要长时间使用收缩血管药物时应建立中心静脉通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临床医生对不稳定患者实施床旁超声进行快速诊断和管理临床危机情况。强化监测级别的决策取决于所有与患者和手术相关因素,不在本推荐的讨论范畴。
临床进展期休克
麻醉医生常滴定血管活性药物(如苯肾、麻黄碱、血管加压素、去甲肾、和付肾)来处理不稳定患者。经常在增加剂量的儿茶酚胺类药物未能改善血流动力学时,小剂量血管加压素(0.5-2.0UIV.)单次注射有效。血管加压素及其类似物在低流量休克、心跳骤停和对儿茶酚胺不敏感的低血压治疗效果已经获得广泛证实。对进展期休克不稳定患者合理治疗顺序见表中第一部分概述。
左心室衰竭
超声心动图和有创监测如肺动脉导管指导左心室衰竭管理,在左心功低下的患者低血容量可以引起或部分引起休克,在开始任何药物治疗休克之前应补足容量。对于容量正常左心衰休克患者使用强心药物和降低后负荷药物治疗。对于已知明显舒张性心功能不良,采用心肌松弛性药物如米尼农来增加心室舒张来提高心输出量。越来越多机械辅助装置如主动脉球囊泵、心室辅助装置、体外生命支持(也叫ECMO)用于那些具有潜在恢复可能的严重左心室衰竭、右室衰竭和心跳骤停的患者。图1概括了左心室休克的管理路径。
图1
右心室衰竭
和左心室衰竭一样,右心室衰竭最好在联合PAC和(或)超声心动图指导下管理。在大多情况下,肺血管阻力急性升高(常在慢性肺动脉高压基础上)引起和导致持续右心衰。联合使用强心、体循环血管收缩和肺血管扩张如NO来管理右心衰。与左心衰治疗相比,使用体循环缩血管药物可以改善终末期器官灌注和心输量(图2)。
与去甲和苯肾相比,血管加压素收缩体循环血管而不收缩肺血管,从而可提高血压而降低肺/体血管阻力比。近年来,机械辅助装置包括心室辅助和体外膜肺在右心衰患者中使用频率日趋增多。
图2
低血容量和收缩压和脉搏压变异
低血容量可引起围术期低血压、循环危象和休克。近十年来,脉搏压变异(PPV)和收缩压变异(SPV)已逐渐取代CVP作为患者低血压时容量治疗反应的床旁监测指标。而这些测定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且合适通气参数(8ml/kg)下的患者中最为可靠,目前逐渐增多的文献显示SPV和PPV也可适于自主呼吸的患者,只是可靠性略微降低。如PPV或SPV超出阈值12-15%,扩容或增加前负荷将可能增加每搏量。来自脉搏氧的体积描记图也可提示容量反应性。重要的是,当存在右心衰或梗阻性休克(如内源性PEEP,心包填塞、张力性气胸、肺高压危像、腹腔间歇综合征)时,会导致SPV和PPV升高,此时其不能预测容量反应性。潮气量过大(10ml/kg)、残气量和肺顺应性(肺气肿)增加和胸廓顺应性下降(3度烧伤、肥胖、俯卧位)增加PPV和SPV,在此情况下容量反应性应进行校正。在心律失常如房颤、频发室早情况下,通过PPV或每搏量变异来评估心肺交互作用不可靠。
在PPV/SPV10%情况下的低血压,使用容量复苏不能改善低血压或休克。被动抬腿试验(快速、可逆、易于操作抬高患者下肢来评估血压和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亦可以预测容量反应性,但其在OR中并不特别实用。尽管超声可评估下腔静脉直径随呼吸变异来预测容量反应性,但其在各种手术(腹部、心脏、胸腔)和体位(侧、俯、坐位)条件下并不实用。利用食道超声或经胸超声进行上腔(SVC)直径测定在很多手术条件下更实用。食道多普勒评估主动脉血流速率也是预测容量反应性的指标,但再次强调,需要食道设备和熟练解读这些数据。就实际而言,当病人处于急性和严重的低血压时应进行容量复苏(如失血或很可能时未检测的外科失血时,输注血液制品)并同时强化监护,容量反应性可以通过血压和心率的变化来进行评估。
在严重休克或心跳骤停时的通气策略
在近二十多年来,多项临床研究显示对于呼衰或ARDS患者使用小潮气量通气和允许高碳酸血症的一种通气策略(通气期间CO2升高,PH下降,但保证氧饱和度在90%以上)既不增加损害,也不增加死亡,也无结局上收益。
无论时休克还是心跳骤停患者使用过度通气都是有害的。休克期间的通气研究反复提示胸内压上升持续时间与通气频率、潮气量、吸气时间和延迟胸廓回缩呈正比,与冠脉和脑动脉的灌注成反比。
在CPR期间,频率为20次/分的通气存活率显著低于10次/分的通气。基本生命支持(BLS)指南始终强调在CPR期间应避免过度通气,推荐更高的按压和通气比例(如30:2)适合所有年龄的患者(新生儿除外)。即使在气管插管条件下,呼吸频率应在《10次/分、吸气时间为1s和潮气量仅为可见的“胸廓起伏”(对于70kg成人约ml)。CPR期间气道管理流程见图3。可同时提供自动CPR和内置负压吸气活瓣气道(可增加胸外按压时静脉回流)的新型装置可能会增加自主循环恢复(ROSC)的几率,但并不增加出院时的存活率。由于正压通气减少静脉回流,且低通气似乎并不引起损害,因而,对于休克患者采用最低参数设置的机械通气以达到氧饱和度》90%是合理的。
图3
内源性PEEP
Auto-PEEP,即内源性PEEP或气体俘获,是一个很好描述但很难识别的循环虚脱和无脉性电活动的原因。Auto-PEEP几乎专发生于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哮喘和COPD(肺大泡)。对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来说,机械通气时并无充足的时间使气体完全呼出,逐渐产生气体(容量)和压力(呼吸末)在肺泡中积聚。这一压力传递给肺毛细血管,进而传给胸腔大血管,从而减少静脉回流和心排量。临床报告显示,随着内源性PEEP增加,静脉回流减少。
当两次呼吸之间呼气气流波形不能回至0基线时,可以推断存在内源性PEEP。当无机械通气气流波形显示时,可以通过断开呼吸机与气管导管接头10-20s来观察有创或无创血压回升来判断内源性PEEP的存在。如通过这种操作使血压得到明显改善就应立即行阻塞性疾病/支气管痉挛最佳治疗和调整机械通气为小潮气量(6ml/kg)、低呼吸频率(10/min)和短的吸气时间(其将会产生反常的和可接受的吸气压力增加)。由于内源性PEEP是循环虚脱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任何不稳定的患者都应立即排除它。拉撒路现象,是在终止复苏后貌似奇迹性恢复和自主循环恢复可能诊断循环虚脱来自复苏期间的内源性PEEP。
手术室内心跳骤停有序急救
手术室内心跳骤停识别比非手术条件更困难,手术室内存在大量传感器如ECG和氧饱和度的虚假报警。麻醉期间心动过缓发生相对频繁,经常与麻醉加上小的或无手术刺激相关的低血压有关。当患者心率低至40次/min,临床稳定时血压在可接受范围内并不需要特别干预。最后,由于患者体型和疾病状态使常规监测无效,在低温、低血容量、或血管疾病的患者,很难或不可能获得可靠的氧饱和度波形;大面积烧伤或全身水泡使无创血压、ECG和脉搏氧监测变得几乎不可能。
围术期环境下的心跳骤停表现包括:无脉性心律(如室速、室颤、严重心动过缓、停搏)、颈动脉波动消失大于10s、EtCO2缺失且无波形和(或)有创动脉波形消失。其中,EtCO2消失可能是最可靠和常规监测循环危象或心跳骤停的指标。
EtCO2评估应紧密结合患者临床情况。当分钟通气量固定和心排量低时,肺血流决定了EtCO2。尽管在低血流状态下可以观察到低EtCO2值,一些临床情况如声门上装置漏气、气道阻力增加(粘液堵塞、支气管痉挛、气管导管扭曲)、肺水肿和过度通气也会导致低EtCO2。高代谢状态如恶性高热或神经性恶性综合征会导致EtCO2增加,静脉使用碳酸氢钠也会增加EtCO2。
一旦确定心跳骤停,应立即毫无延误的启动CPR(图4)。有效的胸外心脏按压可产生EtCO2接近或超过20mmHg,且CPR期间高水平的EtCO2与患者生存率提高相关。很少或几乎无例外,20min的标准ACLS后EtCO2仍然10mmHg与自主循环恢复(ROSC)失败相关。几项研究证实有创血压舒张压(胸廓压缩完全释放时记作舒张压)30-40mmHg与较高自主循环恢复率相关,即使在长时间CPR后。现代除颤仪能提供胸外心脏按压质量实时反馈,这样能够实时驱动CPR急救人员进行轮换,从而提高患者预后。
图4
下表展示了在手术室内和围术期条件下的心跳骤停的逐步评估和管理路径。其建立在和AHA的ACLS流程及关于心跳骤停复苏后综合征的国际复苏联盟委员会的共识申明之上制定。对住院患者长时间的复苏(长达45min)与改善患者生存相关。
自主循环的恢复(ROSC)
EtCO2波形作为自主循环恢复指标较颈动脉或股动脉搏动更为可靠。突然增加的EtCO2(35-40mmHg)提示ROSC。其他提示ROSC的指标包括:触及脉搏搏动、血压及动脉波形出现。胸外心脏按压期间可触及脉搏可能反应静脉搏动。如急救者考虑EtCO2仪器失灵,可以通过对CO2采样管侧流吹气来快速识别仪器功能。
手术室内ACLS流程:症状性心动过缓进展为不可电击的心脏停搏
基于AHA提出心跳骤停原因鉴别诊断6Hs和6Ts,围术期心动过缓、心脏停搏和无脉性电活动有16种原因(8Hs和8Ts)。低氧、低血容量、高/低钾、酸中毒、低温、低血糖、恶性高热、高迷走状态、中毒(过敏/麻醉药)、张力性气胸、肺栓塞/血栓、冠脉栓塞、心包填塞、创伤、QT延长和肺动脉高压。图5中列出了可能导致围术期心动过缓原因及建议的处理方法。窄QRS复合波型无脉性电活动心律提示右室流入或流出道梗阻(如心包填塞、张力性气胸、内源性PEEP、心肌缺血或肺栓塞)。宽的QRS复合波型无脉性电活动预示代谢危象如高钾或局麻药中毒、左室泵衰竭。
图5
围术期突发严重的心动过缓常为手术物理操作引起迷走张力增加或迷走张力麻醉药与解交感张力药物联合引起。对使用付肾或较大剂量麻黄碱处理后心跳并未相应适度增加时应考虑选用阿托品。曾有使用小于1mg的阿托品导致反常心动过缓或窦性停搏的报道,其潜在的机制包括对窦房结的解迷走诱发的应激刺激、窦房结的迷走张力效应和房室结解迷走效应引起的交界节律、阿托品引起的外周低血压和伴随的高迷走张力反射及通过胆碱酶抑制造成的中枢迷走张力增高等。
多种不同原因引起的围术期心动过缓,在有些患者可更早使用起搏进行干预。尽管我们建议使用起搏,但尚无证据提示当发生心跳骤停时进行起搏治疗会给患者带来预后上的收益(起搏可能会延误胸外按压)。急诊起搏治疗恰当适应症包括:对正性变时药无反应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心动过缓、症状性的窦房结组织传导异常、莫氏II2度和3度传导阻滞、交替性的束支传导阻滞或双分支传导阻滞。
症状性心动过速进展为无脉性可电击心脏骤停(室性心动过速、室颤和尖端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
低血容量或麻醉深度与手术刺激强度显著不平衡是围术期低血压的最常见原因。8Hs和8Ts可导致循环危象,进而演化为无脉性电活动。
总之,恶性心律失常的进展是一个严重病情演化过程、严重心脏病合并症和(或)严重并发症发生的标识。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持续心动过速可进展为症状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动过速外的任何导致显著低血压心动过速都是立即转复适应症(心室率次/分)。心脏转复有时可使患者转为症状性心动过缓,可能急需行起搏治疗。室上性或室性心动过速的超速起搏在合适的围术期患者中也可使用,当对药物或心脏转复耐受的心律失常患者应考虑超速起搏。
图4和图6概述了围术期症状性心动过速处理的实际思路。
图6
结论
由手术室或手术条件下的特定原因引起的围术期心跳骤停较以前更为少见。围术期循环危象或心跳骤停通常由对患者熟悉的责任医生来管理,他们了解患者病情,熟悉手术详细过程,对患者的处理更具有针对性、更有效和及时。围术期危象管理基于专家意见和对其特殊的生理状况理解。
参考文献
原文:PMID:期刊年卷:Anesth.Analg.Mar;(3)
MoitraVK,EinavS,ThiesKCetal.CardiacArrestintheOperatingRoom:ResuscitationandManagementfortheAnesthesiologist:Part1.AnesthAnalg;:–88
温馨提示:本平台已开通文章搜索功能,可